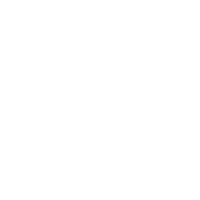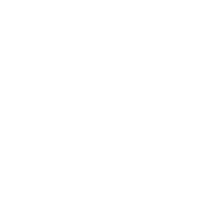【萧乡作家风采】张国华老师——独舞静好成章,风铃摇处诗行
 发布日期:2025-11-08
发布日期:2025-11-08  浏览量:69178
浏览量:69178

扎兰屯的风总带着草木的清润,呼兰小城的雪常裹着岁月的温瑞,当这风与雪拂过书页,便摇响了一串独特的 “风铃”—— 那是萧乡文学社签约作家张国华老师的笔名 “独舞风铃”。她是讲台前授业解惑的英语教师,是笔墨间安放灵魂的诗人,是作协里带动同好的领路人。翻开她的诗集《蝶梦》、散文集《心航》,两千多首古诗词如星子散落,发表在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北京文学》的文字似溪流奔涌,每一句都浸着对生命的热爱,每一段都藏着对世界的悲悯。她以节气为笺,以草木为笔,以日常为墨,在平凡的岁月里写就了不平凡的诗意,让 “独舞风铃” 这四个字,成为萧乡文学社里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。
一、师者仁心,文者慧魂 —— 双重身份里的生命厚度
张国华老师有两个身份,一个在教室,一个在书房。前者是 “传道授业解惑” 的英语教师,后者是 “以笔墨诉衷肠” 的作家,而这两个身份,在她身上从来不是割裂的,而是相互滋养,酿出了独特的生命厚度。
在学生眼里,她是那个腕间总绕着故事的老师。“昨天,还有学生问我:‘老师的手镯真多啊,而且好漂亮啊,都是从哪里买的?’我笑答:‘是岁月的积累。’” 她的首饰抽屉里,铂金的冷艳、黄金的温暖、白银的纯净、水晶的剔透,每一件都藏着时光的印记 —— 少女时用五彩线编织的手链,是青春的灵动;结婚时母亲送的银镯,是亲情的厚重;远行时戴的鸡血石手镯,是对平安的期许。对她而言,腕间的饰品不是装饰,而是 “演绎风韵的载体”,是向学生传递 “热爱生活” 的无声教材 —— 美,从来不是奢侈品,而是从岁月里慢慢沉淀的真诚。
而在文字里,她把师者的 “仁心” 写得格外动人。她曾在《孩子的目光,被风雨擦亮》里写道:“孩子,不能因为你小 / 我就将以后你要面对的艰险隐藏 / 今夜暴雨,狂风大作 / 让我挽起你的手,撑起一把伞 / 看看那花草旷野,怎样变成泥汪 / 看看那娴静清流怎样在天空腾起巨浪”。这不是简单的诗句,而是一位教师对 “挫折教育” 的深刻理解 —— 她不希望孩子活在温室里,而是想带着他们看风雨,看 “一尾尾弱小挣脱黑暗的枷锁”,看 “闪电的速度和姿态将墨空撕裂”。这种教育观,藏在她的每一个教学细节里:或许是课堂上用诗句讲解英语里的 “诗意表达”,或许是批改作业时在评语里添一句自己写的短诗,或许是带学生观察校园里的梨花,告诉他们 “清明,湿透了多少人的眼睛”,也 “藏着多少生命的轮回”。
师者的身份让她更懂 “生命的成长”,文者的身份让她更会 “表达这份懂得”。她在《隧道》里写 “将肉体的黑暗掏空,灵魂才会光明 / 可惜,那么多人,困于光影 / 一生迷失在幻境”,这既是对世人的警醒,也是对学生的期许 —— 她希望自己的学生,既能在知识的隧道里找到方向,也能在精神的隧道里守住清醒。这种 “双重滋养”,让她的文字少了文人的孤高,多了师者的温暖;让她的教学少了机械的灌输,多了诗意的启发。正如她自己所说:“痴爱文字,于文字中安放灵魂”,而这灵魂里,一半是讲台的光,一半是笔墨的香。
二、节气为笺,山河作墨 —— 文字里的时光回响
在张国华老师的文字里,藏着一整部 “节气里的中国”。端午的汨罗、清明的梨花、腊八的粥香、中秋的圆月,她以节气为笺,以山河为墨,把传统节日里的文化情怀与生命哲思,写得既有古韵,又有新意。
端午:不是殉道,是对 “活着” 的思考提起端午,多数人写的是屈原的悲壮,是 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 的求索,而张国华老师却在《端午丨独舞风铃》里抛出了不一样的追问:“你教我们以香草美人自喻 / 却忘了菖蒲的根,也能在淤泥里活着 / 像渔父的船桨,未必不能渡人,也渡己”。她不是否定屈原的高洁 ——“你是高洁的玉石,沉入汨罗便成了星辰”,但她更想探讨 “生命的韧性”:“若你肯慢走一步 / 或许,楚辞会多出半部《离骚》/ 而少一篇《怀沙》的绝笔”。
在《端午悼屈原》里,她进一步延伸这份思考:“你悲壮一跳 / 将世人的心扯断 / 惊涛骇浪拍打着古老河岸 / 风骨气节悲鸣在浩渺云端”,但结尾却落在 “看 / 你走过的地方浪花飞溅 / 吟唱着不朽的龙的诗篇”。她写屈原,不是只写 “殉道的痛”,而是写 “精神的传”—— 屈原的价值,从来不是 “葬身鱼腹”,而是让 “一个民族的泪,流了千年” 后,仍能记得 “该浇灌哪一棵橘树”。这种思考,让她的端午诗脱离了 “悲秋伤春” 的窠臼,多了对 “文化传承” 与 “生命选择” 的深层叩问。
清明:不是悲伤,是对 “轮回” 的释然清明的雨总带着伤感,而张国华老师笔下的清明,却有 “梨花风起” 的温柔。她在《梨花风起正清明》里写:“一树一树的梨花 / 在风中摇曳不停 / 忧伤的白,落满小径 / 清明,湿透了多少人的眼睛”,开篇是常见的清明意境,但接着笔锋一转:“人间匆匆一行 / 一场繁华,一场落梦 / 枝头的娉婷 / 谢幕的凋零 / 尘世的我们 / 谁都逃不出化尘的宿命”。
这份 “宿命感” 不是消极的,而是通透的。她写 “梨花,最终落地成埃 / 明年,依旧花香鸟鸣 / 临摹了一个轮回的重逢”,写 “多年后的我们 / 也会看到这样的风景”。在她眼里,清明不是 “与故人的告别”,而是 “与生命的和解”—— 离别是必然的,但 “花香鸟鸣” 是永恒的;我们会化尘,但 “轮回的重逢” 会一直在。这种释然,在《清明祭》里更直白:“多少年以后 / 我也会放下今生的俗累 / 在蓝天白云下化成轻烟一缕 / 消失在苍茫的天际 / 进入下次的轮回”。没有撕心裂肺的痛,只有对生命规律的尊重,对 “重逢” 的期待,让清明的雨,多了几分温暖的诗意。
腊八:不是熬粥,是对 “岁月” 的治愈腊八的粥,是 “坚硬的岁月” 熬成的温柔。她在《腊八粥》里写:“腊八 / 抓一把坚硬的岁月放锅中熬煮 / 水做药引 / 将黄、白、黑细碎的日子 / 淘洗、浸泡”。这里的 “岁月” 是具体的 —— 或许是教学里的琐碎,或许是写作中的瓶颈,或许是生活里的烦恼,但她用 “温火” 去熬:“温火催开平淡,燃尽无味 / 干瘪、失水的红枣心、饭豆身 / 在沸腾、翻转中,饱满、回软”。
最动人的是结尾:“别忘多放点糖 / 那黏稠的甜 / 足以治愈流年的苦”。这不是简单的 “熬粥技巧”,而是她的生活哲学 —— 岁月总有 “苦”,但只要我们愿意 “多放一点糖”(多一点热爱,多一点宽容,多一点期待),那些 “坚硬” 的日子,终究会变成 “黏稠的甜”。这种把 “日常” 写成 “哲学” 的能力,是她文字的魅力所在 —— 腊八的粥,熬的不是粮食,是岁月;品的不是甜,是治愈。
中秋:不是圆满,是对 “离别” 的体谅中秋的圆月,总与 “团圆” 绑定,但张国华老师却写透了 “离别” 的无奈。她在《留守》里写:“每年中秋节的圆月,将父母唤回 / 此后,又被离别咬缺”,一个 “咬缺”,把离别写得有了痛感,却又真实得让人心疼。她写留守的孩子:“以野草眷恋大地的姿势 / 在风中站立 / 看海水奔向远方 / 听叮咛的声音在波涛中翻滚 / 皎洁的相聚之梦,碎成朵朵泪花”。
但她没有停留在 “痛” 里,而是在《圆月,秋花,旅人》里写:“赶路的旅人 / 用手机,摄下了圆月与秋花 / 瞬间,月色点亮了朋友圈 / 配文:在每一条通往圆满且光明的路上 / 阴雨、孤单是渡船”。她把 “离别” 看成 “圆满” 的必经之路 —— 圆月会被 “咬缺”,但总会再圆;旅人会孤单,但总会抵达。这种体谅,让她的中秋诗少了 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 的哀怨,多了 “接受不圆满,走向圆满” 的从容。
节气于她,从来不是 “应景的题材”,而是 “时光的镜子”—— 照见文化的传承,照见生命的思考,照见岁月的温度。她用文字把节气写成了 “活的文化”,让我们在端午想起 “菖蒲的韧性”,在清明看见 “梨花的轮回”,在腊八尝到 “岁月的甜”,在中秋懂得 “离别的意义”。
三、草木含情,岁月藏意 —— 日常里的诗意栖居
张国华老师的文字,最动人的不是长文叙事,而是对 “日常” 的珍视。一条裙子、一方草坪、一棵桂花树、一串手镯,这些别人眼里的 “平凡之物”,在她笔下都有了生命,有了情感,有了诗意。她用 “草木含情,器物藏意” 的视角,告诉我们:诗意从来不在远方,而在日常的每一个角落。
裙子:是生命的喜欢,是时光的风景裙子是张国华老师 “心灵深处的绮丽的梦”,是 “久远的情结”。她在《我的裙子情结》里写:“当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那些关于裙子的缤纷的记忆,就像蔷薇的藤蔓,密密地爬上我的心窗”。
六岁时的白底碎花背带裙,是她对裙子的最初向往:“奔走跳跃时忽闪着如一只斑斓的蝴蝶在花间起舞,那时,大家看我就像看稀有动物一样。而我却兴奋地在人群中蹦蹦跳跳…… 那只动感的蝴蝶的记忆一直驻留在我的心间,芬芳弥漫”。这不是简单的童年回忆,而是对 “美” 的最初感知 —— 裙子让她第一次体会到 “被关注” 的快乐,体会到 “成为风景” 的幸福。
中学时的紫色碎花裙,是青春的注脚:“当时,流行着琼瑶《穿紫衣的女人》中的那种‘紫色的忧郁’,我的一袭紫色碎花裙,穿上后就像一朵静静盛开的紫荷,真的很美,那时得到了很多女孩艳羡的眼光”。她还抄席慕容的诗:“十六岁的花季只开一次,但我仍在意裙裾的洁白”,这 “洁白” 是青春的纯洁,是少女的自持,是对 “美” 的坚守。
大学时的白色连衣裙,是青春的告别:“大学毕业那年,在绿树白花的篱笆前告别,高晓松的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飘荡在六月的空气中,我清楚的记得,那个夏天,我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,最后一次走过芳香飘溢的丁香道”。白色是 “告别” 的颜色,也是 “初心” 的颜色 —— 这条裙子,藏着她对青春的不舍,也藏着对未来的期许。
中年后的各色裙子,是岁月的从容:“毕业参加工作后,我的衣橱里几乎全是裙子,长的、短的、花色的、纯色连衣的,半身的、素雅的、亮丽的、A 字的、百褶的……” 她写 “李白写的那句美丽的诗‘云想衣裳花想容’,一定是写给一个裙裾飞扬、容貌如花的女子”,但她更懂:裙子的美,不是 “容貌如花”,而是 “女性的优美线条,柔情风韵,就呼之欲出”。如今的她,“喜欢长发飘飘,穿着飘逸的长裙行走在轻风中婷婷摇摆,飘飘洒洒,像一朵风中的玫瑰,不去顾虑身份与衣着是否协调,只是那样放肆地美丽”。这份 “放肆”,是岁月沉淀后的自信,是对 “美” 的始终热爱。
裙子于她,不是 “服饰”,而是 “生命的记录者”—— 记录了童年的天真,青春的纯洁,中年的从容。她用裙子告诉我们:无论时光如何流逝,对 “美” 的热爱,永远是生命里最动人的风景。
手镯:是岁月的故事,是情感的寄托如果说裙子是 “外在的风景”,那手镯就是 “内在的故事”。张国华老师在《流动在手腕上的风景》里写:“美丽的首饰是女子用来演绎风韵的载体,而在这些美丽的饰品中,我对腕上的饰物情有独钟”。
少女时的编织手链,是 “纯真的记忆”:“少女时期,那些手镯手链大多淳朴而自然,喜欢用五彩编织线丝丝绕绕地编织各种复杂或简单的手链…… 春天的细柳,夏天的麦杆,秋天的玉米缨子,冬天的毛毛草都曾是我少女时期腕上的风采”。这些 “就地取材” 的手镯,没有昂贵的材质,却有最纯粹的快乐 ——“在明媚的春光里或是火热的夏季里,着一袭素雅的裙装,尽情地展现腕上或婉约、或优雅脱俗、或调皮可爱的风情,心情轻松自在”。
结婚时的银镯,是 “亲情的厚重”:“我有两个细细的银镯子和两个粗粗的银镯子,是我结婚的时候妈妈送给我的,我更喜欢细细的那两个,上面有星星点点的花纹,我总喜欢把它们戴在一边的手腕上,于是举手投足间便能听见细细的叮当声”。她听说 “喜欢银手镯的女子内心多情而脆弱”,但她更懂:这银镯里藏着妈妈的牵挂,藏着 “一生一世” 的祝福,“它们总是泛着银光,纯净素洁,既充满诗样的情怀又有超凡脱俗之感”。
成年后的玉镯、鸡血石镯、水晶镯,是 “生活的智慧”:“当心情被生活的琐碎烦躁的时候,喜欢轻轻地将泛着烟水绿的玉手镯戴上手腕,玉这有灵性的石头,沉默且多情,带着体温,带着天然的质感,给人宁静与安祥”;“当远行的时候,我喜欢戴鸡血石手镯,在藏族里鸡血石是一种避邪消灾保平安的石头,红红的颜色,充满了悠远的诱惑”;“在早春的时候,我喜欢戴一串紫水晶手链,于清晨穿过街头巷尾,看着刚刚冒出大地的隐隐绿色,心情就如同蛰居了整整一冬的发芽的小草”。
每一只手镯,都是一段岁月的故事,一份情感的寄托。她写 “空闲的时候,也喜欢拨弄这些宝贝链子,像个长不大的孩子”,但她更清楚:“哪个女子不崇尚美丽?” 这份对 “美丽” 的崇尚,不是虚荣,而是对生活的热爱 —— 腕间的风景,从来不是给别人看的,而是给自己的心灵找一个 “安放的角落”。
草木:是心灵的耕耘,是生命的隐喻张国华老师的文字里,草木从不只是 “景物”,而是 “心灵的隐喻”。她在《我的草坪》里写:“曾经,心野荒芜 / 于是,种植一方苍翠,将蓬勃铺展”。这草坪,是她的心灵花园 ——“草坪上,那些我亲手种下的花朵 / 绚烂,馨香 / 以被圈养的姿态匍匐一地 / 每被风摇晃一次,我便心悸一次”。她怕 “风摇晃” 花朵,其实是怕 “生活的风雨” 吹散心灵的 “苍翠”,但她最终学会 “闭上眼,将心突围 / 只闻花香,只沐阳光 / 忽略一切虚无的幻境 / 心门每开一寸 / 世界便开始辽阔一寸”。
她写《秋菊》,不是写 “君子的清高”,而是写 “草的深情”:“‘君子’和‘清高孤傲’是世人赠的美号 / 我只是一蓬草啊 / 在薄凉的岁月里,将深情打捞”。这 “草的深情”,是她的自喻 —— 不追求 “世人的美号”,只愿在 “薄凉的岁月” 里守住一份真诚,一份热爱。
她写《桂花树》,是写 “委屈后的绽放”:“‘桂,鬼,岂能立檐下’/‘身高叶阔,气压翠瓦,遮光挡霞’/‘花期太短,放眼天涯,当换瑶草琪葩’/ 闲言议久,便成真话 / 那人,双眼不眨,一声令下 / 荒原,在阵阵瑟抖中变成了新家”。桂花树被移栽,被质疑,但它 “被打碎的齿牙和泪下咽,一言不发 / 生生地将密密的苍凉 / 开出点点金黄 / 十里香漫,再无碎语喧哗”。这桂花树,是她的人生写照 —— 面对质疑,不辩解,只 “用绽放说话”,让 “十里香漫” 回应所有的 “闲言”。
草木于她,是 “心灵的镜子”—— 草坪照见 “突围的勇气”,秋菊照见 “深情的坚守”,桂花树照见 “沉默的绽放”。她用草木告诉我们:生命或许有 “荒芜”,有 “薄凉”,有 “委屈”,但只要我们愿意 “种植苍翠”,愿意 “打捞深情”,愿意 “开出金黄”,就一定能在岁月里活出自己的 “芬芳”。
四、痛感与温度 —— 生命哲思里的悲悯之光
张国华老师的文字,不只有 “日常的诗意”,还有 “生命的痛感”,但这份 “痛感” 里,永远藏着 “温暖的光”。她写母亲的坚韧,写留守的孤单,写劳动者的辛苦,写弱小者的挣扎,每一笔都带着 “悲悯”,每一句都藏着 “希望”。她用 “痛感与温度” 的交织,让文字有了 “击中人心” 的力量。
母亲:是平凡的战士,是生命的守护者提到母亲,多数人写的是 “温柔的呵护”,而张国华老师却写了 “母亲的战士姿态”。她在《母亲》里写:“夜里,漏雨的鸡棚里,一只母鸡将自己站成了英勇的战士 / 张开的羽翼下一方晴空,两只小鸡,几片碎瓦”。这里的 “母鸡”,就是母亲的化身 —— 没有华丽的辞藻,只有 “漏雨的鸡棚”“碎瓦” 的困境,和 “站成战士” 的坚韧。
接着,她写风雨的残酷:“惊雷,煮沸了泥水,一次次喷涌 / 闪电,把天撕裂道道惨白的骸骨,抓扯着大地 / 瑟抖的羽毛,如抽搐的花瓣 / 瞬间,被火光吞噬 / 废墟下,藏不住一团挺立的焦黑”。这 “焦黑” 是母亲的代价 —— 为了守护 “羽翼下的晴空”,她不惜让自己 “被火光吞噬”,变成 “挺立的焦黑”。
但结尾却有希望:“白天,从黑暗中苏醒 / 强光,刺哭了一双双眼 / 三具身体,粘连在一起,分不开,扯不断 / 挺立的焦黑,像杆竖着的枪 / 对着昨夜风雨的方向”。“三具身体粘连”,是母亲与孩子的 “生死相依”;“像杆竖着的枪”,是母亲的 “不屈”—— 即使经历了风雨,她依然 “对着风雨的方向”,守护着自己的孩子。
这篇《母亲》,没有 “母爱伟大” 的口号,却用 “母鸡护雏” 的细节,把母亲的 “坚韧” 与 “守护” 写得入木三分。她懂母亲的 “痛”—— 漏雨的鸡棚,火光的吞噬;更懂母亲的 “暖”—— 羽翼下的晴空,挺立的焦黑。这种 “懂”,是对母亲最深的致敬,也是对 “生命守护者” 最动人的礼赞。
劳动者:是人间的烟火,是岁月的舞者张国华老师眼里的劳动者,不是 “辛苦的符号”,而是 “人间的烟火”,是 “岁月的舞者”。她在《搬运人间烟火的人》里写外卖员:“他像风,载着浓稠的人间烟火 /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”。“风” 是他的速度,“人间烟火” 是他的使命 —— 他不是在 “送外卖”,而是在 “搬运人间的温暖”。
她写他的 “日常”:“黄衣黄帽,又如奔走的向日葵 / 面朝太阳,眼中有光 / 黑夜与黎明,不过是浮光掠影 / 驮着的餐箱里,盛着四季,散着百味 / 春花化为果蔬,夏雨调作汤羹 / 秋霜酿成蜜糖,冬雪淬为精盐”。“向日葵” 的比喻,让外卖员有了 “向阳” 的希望;“餐箱里的四季”,让他的工作有了 “诗意的温度”—— 他驮着的不是 “餐食”,而是 “四季的味道”,是 “别人的期待”。
最动人的是结尾:“他爱脚下每一条颠簸的路 / 摇摇晃晃的身影,像极了舞蹈 / 他也爱深夜里屋中亮起的明灯 / 总有人,空着肠胃,等着奔赴”。“摇摇晃晃的身影像舞蹈”,这是对劳动者最美的赞美 —— 他的辛苦,在她眼里变成了 “舞蹈”;他的坚持,是因为 “屋中亮起的明灯”,是因为 “别人的等待”。
她懂劳动者的 “痛”—— 颠簸的路,黑夜的冷;更懂劳动者的 “暖”—— 眼中的光,屋中的灯。这种 “懂”,没有居高临下的同情,只有平等的尊重,让我们看见:每一个 “搬运人间烟火的人”,都是岁月里最动人的 “舞者”。
弱小者:是黑暗的微光,是希望的种子张国华老师从不忽视 “弱小者” 的存在,她写他们的 “痛”,更写他们的 “光”。她在《被山鹰啄瞎的双眼》里写一个失明的女子:“被山鹰啄瞎的双眼,白布紧缠 / 看不清人心深浅 / 感觉不到季节冷暖 / 她将自己蜷缩成一朵不开放的汀兰 / 对内曲卷,对外掩敛”。这是她的 “痛”—— 失明的无助,对世界的恐惧,让她 “蜷缩”,让她 “掩敛”。
但她没有一直 “痛” 下去:“只有当花香扑面,鸥鸟轻唤 / 才敢在无人的江边,将自己舒展 / 任乌黑的长发轻舞飞旋 / 任发霉的身体在旷野晾晒 / 然后伸出胆怯的双手 / 抚摸一下这虚幻又真实的人间”。“花香”“鸥鸟” 是世界的 “温柔”,让她有勇气 “舒展”,有勇气 “抚摸人间”;“发霉的身体在旷野晾晒”,是她对 “光明” 的渴望,对 “生活” 的不舍。
结尾更有温暖:“路过的风,轻轻抱住了她 / 抱住了那看不见的泪眼长潸”。这 “风”,是张国华老师的 “悲悯”,是世界的 “善意”—— 即使她看不见,也有人 “抱住” 她的眼泪,给她温暖。
她还在《失心的雕像》里写一个孤独的守护者:“背倚灯塔,头顶蓝天 / 我手握刀铲,脚踏泥污,站在海边 / 仍用一缕坚定的目光,向远方张望”。她 “手握刀铲,脚踏泥污”,是生活的 “苦”;但 “坚定的目光,向远方张望”,是她的 “希望”—— 即使 “被掏空的身体承不起一两霜风二两雨”,她依然守护着 “年轻的脸庞”,守护着 “睡梦中都会笑醒的希望”。
这些 “弱小者” 的故事,没有 “卖惨”,只有 “坚守”;没有 “绝望”,只有 “希望”。张国华老师用文字告诉我们:即使在黑暗里,也有 “微光”;即使在困境中,也有 “种子”—— 这 “微光” 与 “种子”,就是生命最动人的力量。
五、墨痕留芳,美文长在 —— 萧乡文学社里的风铃力量
作为扎兰屯市作家协会主席、哈尔滨市萧乡文学社签约作家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张国华老师的文字不只是 “个人的表达”,更是 “萧乡文学社的光”。她用自己的创作,带动着更多热爱文字的人;用自己的坚守,为萧乡文学注入着 “温暖的力量”。
她是萧乡文学的 “参与者”。在《九月,文字在拥抱碰撞中生香》里,她写:“九月,辉河畔五十多个有趣的灵魂,将文字放飞 / 诗词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 / 在彼此的拥抱碰撞中绽花生香”。这里的 “五十多个有趣的灵魂”,是萧乡文学社的同好,而她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 ——“没有刻意寻觅,未曾奔赴远方 / 诗花,便在草原上同碧草蔓延 / 心底的问号,逗号,感叹句 / 不断喷涌 / 恨不能将天边的夕阳拽住 / 怕它将句号匆匆书写”。她怕 “夕阳拽住句号”,其实是怕 “文字的热情熄灭”,怕 “同好的相聚散场”。
她是萧乡文学的 “带动者”。她著有诗集《蝶梦》、散文集《心航》,创作古诗词两千多首,在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多家纸媒发表文字,这些 “成绩” 不是她的 “炫耀”,而是她的 “底气”—— 她用自己的创作告诉同好:“只要坚持,文字就会‘绽花生香’”。她还在《踏香而来》里写:“一朵夜来香,循着词章,踏着月光 / 在北方一个天寒地冻之夜 / 携着暖,带着香 / 缓缓叩开了我的心房”。这 “夜来香”,就是她对同好的期待 —— 即使在 “天寒地冻” 的日子里,也要 “携着暖,带着香”,用文字叩开彼此的心房。
她是萧乡文学的 “守护者”。她在《一个人的天荒地老》里写:“麻雀们聚在树上聒噪 / 嘲讽着蜂蝶妖娆 / 青蛙们在池中鼓起长调 / 同夜色叫嚣 / 我挺了挺身腰,走进自己的城堡”。这 “城堡”,就是她的 “文字世界”,也是萧乡文学的 “精神家园”—— 即使有 “麻雀的聒噪”“青蛙的叫嚣”,她依然 “挺了挺身腰”,守护着这方 “没有嘈杂干扰” 的天地,守护着 “灵魂生出陡峭” 的纯粹。
她曾说:“痴爱文字,于文字中安放灵魂”。对她而言,文字不是 “谋生的工具”,而是 “灵魂的栖息地”;萧乡文学不是 “名利的场域”,而是 “同好的家园”。她用自己的墨痕,为萧乡文社留下了 “芬芳”;用自己的心灯,为热爱文字的人照亮了 “方向”。
如今,扎兰屯和萧乡都已立冬,“独舞风铃” 的文字仍在写 —— 她的文字,就像一串永远摇响的风铃,在岁月里传递着 “诗意”,传递着 “温暖”,传递着 “希望”。
风铃摇处皆诗行,这就是萧乡作家独舞风铃(张国华)的风采 —— 她用笔墨丈量山河,用热爱温暖岁月,于文字中安放灵魂,也为世间留下了一串串永不褪色的诗行。而这诗行,终将在萧乡的风里,在更多人的心里,永远摇响,永远芬芳。
上一篇 : 新加坡《有米》诗刊简介及2025年第5期目录
下一篇:以笔为舟,载时代新声——致全国媒体人